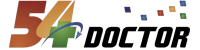-
医院简介
医院介绍

类型:公立 综合医院等级:三级甲等医保:医保定点医院医院电话:010-85231777(公众与健康服务热线)预约挂号电话:010-114(24小时) 在线挂号医院网址:http://www.bjcyh.com.cn院本部地址: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南路8号 查看地图乘车路线石景山院区地址: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5号 查看地图乘车路线常营院区地址:北京市朝阳区东十里堡路3号院 查看地图乘车路线一、医院概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建于1958年,是北京市政府举办的集医疗、教学、科研、预防于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;是首都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,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在医院,也是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A类定点医疗机构。医院现为一院三址,北京朝阳医院、石景山院区和常营院区三个院区。其中,北京朝阳医院和石景山院区总占地面积10.28万平米、建筑面积21万平米;常营院区占地面积7.22万… 详细>>
-
新闻中心
-
党建工作
- 科学研究
-
医学教育
您所在的位置:
首页
>> >>
医院新闻
绿萝与新生:病房里的叙事护理

肿瘤科的消毒水气味总带着一股沉甸甸的药味,走廊尽头监护仪的“滴滴”声,像永不停歇的秒针,敲打着每个被疾病困住的日子。但走过护士站那排架子时,目光总会被一片温润的绿意牵住。二十多个玻璃瓶里,绿萝的根须在清水里舒展如银线,新抽的嫩叶卷着边,像攥着不肯服输的小拳头。这片在病痛里扎下根的绿洲,藏着小贾用生命写就的故事,也藏着叙事护理最动人的模样。
第一次见小贾,她蜷在病床上,窗帘拉得严严实实。我作为责任护士,带着尊重、谦卑与好奇走近她:“我是你的责任护士张美美,看样子咱俩年龄差不多。我看到你把窗帘拉得很严实,能跟我说说为什么吗?”她声音闷在枕头里,带着几分疲惫:“我是胰腺癌伴远处转移,这病真是受罪。家里人天天来陪我,可我一闭眼就胡思乱想,这罪啥时候是个头呀?”她不愿被过多惊扰,那份绝望像冰块,砸碎了脸上所有的阳光,世界只剩下“吉西他滨”、“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”这些药名。我试着用刚学的叙事护理技巧追问:“你能跟我具体说说‘那个受罪’吗?”小贾坦言:“想到化疗反应我就害怕,家里人把陪我治病当成全部,可药用了病也没好,真不知道接下来还会面临什么……”我默默听着,那些话语里的痛苦,比任何诊断书都更刺心。这时的她,还不是那个举着绿萝、眼里有光的姑娘。
转机藏在污物间的角落。一天,一截被遗弃的绿萝枝条躺在垃圾桶边,我拾起那些发蔫的枝条,插进空瓶里。小贾不知何时站在门口,指尖轻轻碰了碰发蔫的叶子:“都蔫了,这东西能活吗?”我说:“这是绿萝,皮实着呢!有水就能活。我们打算让病友们认养,看看谁养得最好,你要做第一个认养人?”小贾突然来了精神,眼睛亮得像落了星子:“真的?那我拿回去试试。”慢慢地,病友们跟着她养起了绿萝。3床的大爷把装中药的玻璃罐洗干净当花盆;5床的阿姨戴着老花镜,借护士站的小剪刀修剪黄叶:“黄叶耗养分,得剪了,跟咱治病一样,把坏东西清出去才能长新的。”以前病房里碰面,大家总爱问“昨天吐了几次”、“医生说下周加量不”,语气里带着认命的疲惫。可自从有了这些绿萝,打招呼都变成了“你那瓶抽新叶了没?”、“我这根须都长到瓶底了”。小贾每天精心照顾楼道里的绿植,从最初几个玻璃瓶里的嫩芽,到后来二十多个各式各样的玻璃瓶,硬是在满是病痛的地方,种出了一片象征顽强生命力的小绿洲!
再入院时,那截枝条已经抽出两片新叶,嫩得能掐出水。小贾举着瓶子走到护士长面前,声音还有点哑,眼里却闪着星子:“护士长您快看,它真活了!咱们病房里天天听监护仪响,说的都是“加量、耐药”,可绿萝不管这些,就一门心思长根、抽叶。”她晃了晃瓶子,绿萝叶跟着摆动:“您说,人是不是也能这样?”这话像把钥匙,打开了病房里紧闭的门。说话时,她眼睛会不由自主地瞟向绿萝架,嘴角带着藏不住的笑意,好像那些努力生长的绿意,真的能顺着目光钻进心里,生出点希望来。
变化是悄悄发生的。护士站的白板上依旧写着密密麻麻的医嘱,监护仪的声音也从未停歇,但走廊里的叹息声少了,笑声多了。这何尝不是她对自己生命故事的积极“改写”?她用行动解构着病房的疾病叙事,种下了“生机”的支线故事。护士们也悄悄加入了这场“叙事”:查房时不再只盯着输液泵,会多问一句“今天哪片叶子最精神?”给小贾进行PICC导管维护时,故意说:“你看这导管和输进去的药水,跟绿萝的根须似的,都是在使劲活着呢。”她们知道,这些话不是安慰,是帮她看见:疾病可以带来疼痛,但带不走她“让绿意生长”的能力;肿瘤可以侵蚀身体,却夺不走她为病房创造温暖的力量!
小贾走的那天,初秋的阳光刚好透过窗户,落在那片绿萝上。护士去换输液袋时,看见叶尖都挂着露珠,亮晶晶的,像谁没擦干的眼泪。那个画着笑脸的酸奶瓶还朝着太阳,只是再也不会有人踮着脚,小心翼翼地给它们转方向了。
但故事没有结束。叙事护理的本质,是让护理从“疾病护理”延伸到“人的护理”——它承认每个患者都是独特的生命个体,疾病只是其生命故事的一部分,而护士的角色不仅是治疗者,更是患者生命故事的倾听者、陪伴者和意义的共同建构者,最终帮助患者在疾病中找回对生命的掌控感,实现身心的整体疗愈。叙事护理的核心理念是:“人不等于疾病、疾病不会100%操纵人、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作者、每个人都是自己疾病的专家、每个人都有资源和能力。”
绿萝,将个体叙事转化为集体精神符号,强化了生命的信念。护士们轮流给绿萝换水,新入院的病人会接过“养护接力棒”。现在,那片绿洲还在生长。监护仪的“滴滴”声依旧在走廊回荡,只是听着不再像催命符,反倒像在给那些努力伸展的叶子伴奏。这大概就是叙事护理的意义——我们不用魔法驱散病痛,却能用倾听接住每个生命的故事;我们不能改写诊断书,却能陪着患者在绝望里种出希望,让他们知道:哪怕身处寒冬,他们依然有能力,为自己、为别人,捧出一片春天!

病房里的绿萝
肿瘤科

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3042
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3042